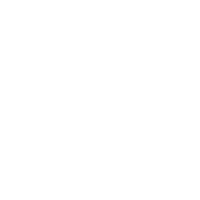修了28年战机因学历无法提干,他递交退伍申请,空军装备部部长连夜坐专机带着特招令找上了门
发布日期:2025-11-21 15:17 点击次数:184
声明:本文根据资料改编创作,情节均为虚构故事,所有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部分图片非真实画像,仅用叙事呈现,本文旨在宣扬人间正义、杜绝犯罪发生!
当空军装备部的陈部长,带着那份滚烫的特招令,从专机上走下来时,我,王建国,正准备脱下这身穿了二十八年的军装。
二十八年,一万零二百二十个日夜。我把一个愣头青小伙子最宝贵的青春,全都献给了机库里这些冰冷又滚烫的“铁鸟”。经我手检修、放飞的战机,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架次,它们的引擎轰鸣是我听过最美的交响乐,机翼划破长空的呼啸是我最好的安眠曲。我曾以为,我会像一颗螺丝钉,永远拧在这里,直到再也拧不动为止。我也曾梦想过,有一天能戴上军官的肩章,名正言顺地把我这身本事,写进教材里,传给更多的人。
可梦想,终究是碎了。
而这一切,都源于三天前,我亲手递交到团长办公室的那份,字迹有些颤抖的退伍申请书。
第一章:最后一份名单
初秋的西北戈壁,风已经带上了刮骨的凉意。
机库里那架刚刚完成大修的“飞豹”歼击轰炸机,静静地趴窝在聚光灯下,像一头蓄势待发的钢铁巨兽。我戴着老花镜,正用指尖轻轻划过机身上的一排铆钉,感受着它们细微的平整度。
这种触感,比任何精密的仪器都让我安心。
“王师傅,您看,新发的《J10C新型航电系统维护手册》,厚得跟砖头似的。里面好多代码,我看着头都大了。”
徒弟李浩凑了过来,他去年刚从空军工程大学毕业,是个高材生,浑身都是理论知识,但一上手就犯怵。他对我,比对团长还尊敬。
我摘下眼镜,接过那本厚厚的册子,随手翻了几页,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航油和金属混合的味道。
“别看它写得天花乱坠,都是吓唬你们这些大学生的。”我拍了拍手册,又指了指战机的机腹,“万变不离其宗。记住,飞机不会说谎,你听它的声音,摸它的温度,感受它的震动,它会把所有问题都告诉你。书是死的,飞机是活的。”
李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眼神里满是崇拜:“师傅,您这手绝活,整个基地都找不出第二个。张团长都说了,您就是咱们机务团的‘定海神针’。”
我笑了笑,没接话。
定海神针?或许吧。可定海神针,终究只是一根针,变不成那根擎天的柱子。
我把手册还给李浩,拍了拍手上的灰,其实手上没什么灰,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动作。我走向机库门口,想透透气。
门口的公告栏,总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今天似乎格外热闹,一群年轻的士官和尉官围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我的心,不受控制地咯噔了一下。
这个时间点,这个阵仗,我知道,是那份名单下来了。
一年一度的士官提干名单。
我脚步有些发虚,二十八年了,从十八岁入伍到现在四十六岁,我见过二十七份这样的名单。每一份名单公布前,我都会像现在这样,心跳得厉害。而每一份名单公布后,我的心又会沉到谷底,然后用一整年的时间,慢慢让它浮上来,等待下一次的下沉。
“王师傅!”有人眼尖,看见了我。
人群“呼啦”一下散开一条缝,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带着复杂的神情看着我。有同情,有惋惜,也有不知所措。
李浩跟在我身后,低声说:“师傅,要不……咱们回去吧。”
我摇了摇头,拨开人群,走到了公告栏前。
那张红头A4纸,在白色的墙壁上显得格外刺眼。我从上到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过去。都是些年轻的面孔,好几个还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兵。他们的名字后面,跟着崭新的职务和军衔。
我看得极其缓慢,极其仔细,仿佛多看一会儿,就能从那张纸上,找出自己的名字一样。
当然,没有。
和过去二十七年一样,没有“王建国”这三个字。
我盯着那张纸,久久没有动弹。耳边的议论声变得模糊,机库里战机的轮廓也开始扭曲。我仿佛看到十八岁的自己,第一次摸到冰冷的机身时,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王,好好干!咱们部队,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
我也看到了二十五岁的自己,为了排除一个连轴转了三天三夜都没找到的液压故障,硬是把自己吊在起落架上睡着了。那一次,我救回了一架价值上亿的战机,荣立二等功。团里给我报了提干,却因为只有高中学历,在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
我还看到了三十五岁的自己,某新型战机试飞,突发“空中停车”的重大险情。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是我根据飞行员描述的异常抖动频率,大胆判断是某个特定批次的燃油泵叶片存在细微的共振裂纹,这个推断在当时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总部专家连夜开会,都觉得是无稽之谈。我立下军令状,如果判断失误,甘愿受任何处分。结果,拆开一看,和我判断的位置、裂纹走向,分毫不差。那一次,我荣立一等功,全军通报表彰。张团长握着我的手,眼睛通红:“老王,委屈你了。放心,这次我豁出这张老脸,也一定给你争一个名额!”
结果,还是因为那道该死的学历门槛,再次被无情地驳回。
“是金子总会发光”,可他们却说,你这块金子,没有文凭的认证,纯度不够。
“王师傅……王师傅……”李浩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我回过神,发现自己的眼眶有些湿润。我赶紧转过身,用手背胡乱抹了一下。
“没事,风大,迷了眼。”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声音却有些沙哑。
人群沉默着,没人相信我的话。这里的风,再大,也吹不红一个老兵的眼。
我转身,一步一步地走回我的工具台。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二十八年的青春碎片上,咯吱作响。
回到工具台前,我没有再去看那架心爱的“飞豹”。我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一堆泛黄的技术图纸和奖章证书下面,拿出了一张稿纸和一支笔。
李浩跟过来,看到我的动作,脸色瞬间变了:“师傅,您……您要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俯下身,一笔一划地,在稿纸上写下了三个字:
退伍申请书。
第二章:拧不动的螺丝
写下“退伍申请书”这五个字的时候,我的手异常地稳。
二十八年,我用这双手拆解过上万个精密零件,拧过几十万颗螺丝,每一次都稳如磐石。但这一次,当笔尖落在纸上,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拆解自己的骨头。
李浩站在一旁,急得团团转,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师傅,别冲动,千万别冲动啊!这事儿肯定还有转机,张团长不是说了吗,他会一直帮您想办法的……”
“办法?”我停下笔,抬起头看着他,自嘲地笑了笑,“小李,你知道一颗拧滑了丝的螺丝吗?”
李浩愣住了,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一颗螺丝,如果拧得太久,磨损得太厉害,丝口就滑了。它看起来还在那个位置上,但实际上,它已经无法再拧紧,也无法再承受任何力道了。再拧下去,只会彻底报废。”我顿了顿,声音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我,就是那颗滑了丝的螺丝。拧不动了。”
说完,我不再理会他,继续在申请书上写着。理由很简单:本人王建国,因年岁已高,精力不济,难以胜任高强度机务保障工作,特申请退出现役,望批准。
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写完,签上名字,按下红色的手印。我把那张薄薄的纸对折起来,揣进胸口的口袋里,那里紧贴着心脏,能感受到它的分量。
我脱下沾满油污的手套,整整齐齐地放在工具台上,又拿起一块麂皮,把我那些视若珍宝的工具,一把一把地擦拭干净,按照编号,分毫不差地放回工具箱里。那套跟了我二十多年的德国进口棘轮扳手,在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光,仿佛在无声地与我告别。
做完这一切,我站起身,对目瞪口呆的李浩说:“看好家。我去去就回。”
团长办公室在三楼。我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感觉双腿灌了铅一样沉重。走廊里,挂着一排排的荣誉锦旗,其中有好几面,都和我的名字有关。
“全军技术能手”,“优秀士官标兵”,“红旗机务组”……
现在看来,这些红色和黄色的荣誉,都像是在无声地嘲讽着我。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张团长压抑着怒火的咆哮声。
“……凭什么?我问你们凭什么!王建国的能力,你们谁不清楚?别跟我提规定,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立过一等功的技术骨干,干了快三十年,你们就用一句‘学历不符’给打发了?这传出去,不是让一线卖命的兵寒心吗!”
里面传来一个唯唯诺诺的声音:“团长,您别激动,这是上面的文件,我们也没办法……”
“没办法?我看你们就是懒政!就是不作为!这份名单,我不同意!”
“砰”的一声,像是拳头砸在桌子上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心里五味杂陈。张团长是个好人,这些年,为了我的事,他没少往上跑,没少跟人拍桌子。我知道,他尽力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更不能让他为难。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军容,敲了敲门。
“进。”里面的声音依旧怒气冲冲。
我推门进去,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张团长正铁青着脸坐在办公桌后,旁边站着一个政工科的干事,一脸的尴尬。
看到我,张团长脸上的怒气瞬间凝固,随即化为一丝愧疚和无奈。他挥了挥手,让那个干事先出去。
“老王……”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桌上的一包烟扔了过来,“坐。”
我没接烟,也没坐。我只是走到他面前,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折叠好的申请书,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张团长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死死地盯着那份申请书,像是在看一个引爆了的炸弹。
“你……你这是干什么?”他的声音有些发颤。
“团长,我想家了。”我平静地说,“我爹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媳妇一个人拉扯孩子,也辛苦了快二十年。我想……是时候回去了。”
这些都是实话,但在此刻说出来,却更像是一个蹩脚的借口。
张团长猛地站了起来,一把抓起那份申请书,狠狠地摔在地上。
“王建国!”他指着我的鼻子,眼睛通红,“你这是在打我的脸!你这是在打我们整个团的脸!二十八年都过来了,就差这临门一脚,你就要放弃?我告诉你,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一天,你的事,我就管定了!这报告,我绝不会签!”
“团长,”我看着他,语气依旧平静,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绝,“您知道我的脾气。这头倔驴,一旦撅了蹄子,是谁也拉不回来的。”
“你……”张团长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我们俩就这么对峙着,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一架战机呼啸着起飞,巨大的轰鸣声穿透了玻璃,震得人心头发颤。
我听着那熟悉的轰鸣声,心中一阵绞痛。
再见了,我的战友。
“团长,这些年,谢谢您的照顾。”我朝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我这辈子敬得最用力,也最沉重的一个军礼。
然后,我转过身,没有再看他一眼,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我没有回头,但我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灼人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直到我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我知道,这份申请书,他今天不签,明天也得签。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一个兵铁了心要走,谁也拦不住。
我的心,已经死了。
第三章:最后的巡视
我递交退伍申请的消息,像一阵风,迅速传遍了整个机务团。
接下来的两天,我的宿舍门槛都快被踏破了。从我带出来的徒子徒孙,到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再到其他科室的领导,一波接一波地来做我的“思想工作”。
他们说的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
“老王,别想不开啊,部队需要你!”
“师傅,您走了,我们怎么办?那几个新型号的发动机,离了您,我们心里没底啊!”
“建国,再等等,说不定明年政策就松动了呢?你这技术,要是退伍了,不是国家的损失吗?”
我只是安静地听着,给他们倒水,递烟,然后微笑着摇头。
我的心意已决。
不是赌气,也不是冲动。就像一根紧绷了二十八年的弦,终于在最后一次失望中,彻底崩断了。再怎么续,也弹不出原来的调子了。
李浩这小子最执着,干脆搬了个马扎,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我宿舍门口,生怕我长翅膀飞了。他红着眼圈,一遍遍地跟我复盘我的那些“光辉事迹”,试图唤醒我对这身军装的留恋。
“师傅,您还记得吗?零八年那次,高原驻训,一架飞机的起落架信号灯出故障,所有人都查不出原因。是您,顶着高原反应,钻进狭窄的设备舱,硬是用万用表一根线一根线地测,最后发现是一根被老鼠咬破皮的信号线,因为气压变化,发生了间歇性短路。您救了飞行员一命,也救了飞机啊!”
“师傅,还有前年,外军搞技术交流,他们那个王牌机械师,故意给咱们的飞机设了个复合型故障,想看咱们笑话。几十个专家研究了半天都没头绪,是您,只听了听发动机的喘息声,就要了杯柴油,用手沾着在故障点周围画了个圈,说问题就在这里面。打开一看,果然是一个微动开关的弹片,被做了手脚。当时那帮老外脸都绿了!”
他说的这些,我当然都记得。这些记忆,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骨子里。
可记得越清楚,心就越痛。
我为这支部队,掏心掏肺,倾尽所有。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它,可它最后,却连一个身份的认可,都给不了我。
到了第三天,张团长终于还是把签了字的申请书,递到了我的手上。
他的脸色很难看,像是几天没睡觉,眼窝深陷,胡子拉碴。
“老王,”他把那张纸递给我,手都在抖,“手续,我让机关的人给你加急办。你……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接过那张纸,感觉它有千斤重。
“谢谢团长。”我低声说,“我没什么要求。就是想在走之前,再去机库看看。”
张团长点了点头,喉结滚动了一下,最终还是没能说出“保重”两个字,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那背影,说不出的萧索。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最后一次走进了我工作了二十八年的机库。
我没有穿工作服,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常服。我走得很慢,像一个游客,在参观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我看着那些年轻的机务兵,在我的徒弟们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航前检查。他们的动作标准,口令清晰,充满了朝气。
我看到李浩,正趴在一架战机的进气道里,检查里面的情况。他的姿势,和我当年教他的时候,一模一样。
真好。
我绕着一架架战机,慢慢地走着,用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它们冰凉的蒙皮。

“老伙计,要走了,以后不能再给你挠痒痒了。”
“你这个小毛病多的家伙,记得提醒小李他们,每飞五十个小时,就要检查一下你的3号液压管接头,那里容易渗油。”
“你最争气,从来没掉过链子。以后也要好好的,保家卫国,就靠你们了。”
我像一个即将远行的父亲,絮絮叨叨地跟自己的孩子们做着最后的告别。
不知不觉,我走到了一架停在最角落的飞机前。
这是一架已经被淘汰的老式歼7,机身上布满了风霜的痕迹。它是我入伍后,接触的第一款飞机。当年,我就是在这架飞机上,学会了机务兵的所有基本功。
我拉开驾驶舱的舷梯,爬了上去,坐在了那个狭小的驾驶舱里。仪表盘上的指针,早已不再转动,座椅的皮革也已经开裂。
我握住驾驶杆,闭上眼睛,仿佛又能听到耳边传来引擎的轰鸣,感受到机身在跑道上加速时的剧烈抖动。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脸颊上的皱纹,无声地滑落。
我在这里,守了二十八年。
我守着它们从青涩到成熟,从老旧到先进。我见证了空军的每一次换装,每一次腾飞。
我以为我会守到老,守到死。
却没想到,最后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不体面地离开。
我就这么在驾驶舱里,静静地坐着,从下午坐到黄昏,又从黄昏坐到深夜。
没有人来打扰我。他们都知道,我需要这最后一次的独处。
直到深夜,我才从飞机上下来。
该走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灯火通明的机库,看了一眼这些与我朝夕相伴的“铁鸟”,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向着营房走去。
我的脚步,从未如此沉重。
第四章:深夜的轰鸣
回到宿舍,我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二十八年,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旧皮箱,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堆荣誉证书,还有一张已经泛黄的全家福。
照片上,妻子抱着年幼的儿子,笑得一脸灿烂。那时候,我还年轻,穿着崭新的军装,英姿勃发。我记得拍照那天,我跟她说:“媳妇,你等我,等我提了干,就把你们娘俩接到部队来,再也不分开了。”
这个承诺,我食言了二十多年。
我把那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将那些奖章和证书,一本一本地放进箱子。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这些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勋章,此刻却像一块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就在我准备合上箱子的时候,一阵异乎寻常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划破了戈壁深夜的宁静。
这不是战斗机的轰鸣。
战斗机的声音,高亢、尖锐,充满了力量感。而这个声音,更低沉,更浑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是大型运输机的声音!
我心里一惊。我们这个是前线作战机场,平时除了战斗机和教练机,很少有大型运输机在深夜这个时间点降落,除非……有紧急任务,或者来了什么大人物。
紧接着,基地里响起了短促而尖锐的警报声。这不是战斗警报,而是迎接重要人物的礼宾号。
整个营区,瞬间被惊动了。
我走到窗边,看到远处机场跑道的方向,亮起了一排排雪亮的引导灯,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一架体型庞大的军用运输机,在引导车的带领下,正缓缓地滑向停机坪。
宿舍楼里,也乱成了一锅粥。走廊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干部们的呵斥声。
“快快快!所有人,紧急集合!”
“整理军容!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一号哨位,加强警戒!”
出什么事了?
我正疑惑间,宿舍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撞开。
李浩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脸上满是震惊和惶恐,话都说不利索了。
“师……师傅!不……不好了!快……快走!”
“慢点说,天塌不下来。”我皱了皱眉,给他递了杯水。
他一口气灌下去,总算喘匀了气,急声道:“师傅!张团长……张团长让我来叫您!快!快跟我去机场!出大事了!”
“去机场干什么?我一个马上要退伍的老兵,凑什么热闹。”我不为所动,继续收拾着我的皮箱。
“哎呀,我的好师傅!就是因为您啊!”李浩急得都快哭了,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皮箱,扔到床上,“您知道刚才那架飞机上,下来的是谁吗?”
我看着他。
李浩咽了口唾沫,声音都在发抖:“是……是空军总部的人!专机!是专机啊!而且……而且张团长说,是……是冲着您来的!”
冲着我来的?
我愣住了。
开什么玩笑。我王建国何德何能,能惊动空军总部的大人物,还坐着专机连夜赶来?
“别胡说八道了。”我以为他是为了留住我,故意编的瞎话。
“我没胡说啊师傅!”李浩指着窗外,满脸焦急,“整个基地的领导,从团长到政委,全都去停机坪列队迎接了!张团长点名让您必须过去!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看着他不似作伪的神情,我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难道……真的出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大事?
来不及多想,李浩已经半拖半拽地拉着我往外跑。
我们一路冲下楼,整个营区已经是一片紧张肃杀的气氛。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卫兵,正跑步奔向自己的岗位。所有的探照灯全部打开,将整个基地照得亮如白昼。
我被这股气氛感染,心脏也不由自主地砰砰直跳。
到底是谁来了?这么大的阵仗?
第五章: tarmac上的对峙
越靠近停机坪,气氛就越凝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到极致的味道,甚至盖过了浓烈的航油味。巨大的运输机像一头沉默的巨兽,静静地停在聚光灯下,机身上“中国空军”四个大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在飞机不远处,我们团,不,是整个基地的所有校级以上的军官,都笔挺地站成一排,连大气都不敢喘。
张团长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军容前所未有的严整,腰杆挺得像一杆标枪,但从他微微颤抖的指尖,我能看出他内心的紧张。
看到我和李浩跑过来,张团长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然后压低声音,用气声对我吼道:“王建国!你还知道来!快!站到我身后来!”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惊惶。
我被他这副样子搞得更加莫名其妙,但还是依言站到了他的身后。我注意到,周围所有领导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意味,震惊、疑惑、甚至还有一丝……敬畏?
我彻底懵了。
就在这时,运输机的舱门缓缓打开,一道舷梯延伸下来。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舱门口。
那是一个穿着空军常服的将军,肩上扛着闪亮的将星。虽然隔着一段距离,看不清他的面容,但那股渊渟岳峙的气势,却像一座大山,瞬间压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头。
他没有立刻走下来,而是站在舷梯顶端,锐利的目光缓缓扫过停机坪上的每一个人。
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似乎停顿了一下。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在那一刻漏跳了一拍。
“敬礼!”张团长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嘶哑的口令。
“唰”的一声,所有军官,整齐划一地举起了右手。
那位将军,迈着沉稳的步伐,一步一步地从舷梯上走了下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两名提着公文包的秘书。
他径直走到了队列前,张团长赶紧上前一步,立正报告:“报告首长!xx机场守备部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团长,张爱军!”
那位将军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却越过了张团长,直接锁定在了我身上。
“你,就是王建国?”
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威严和力量,仿佛一颗颗石子,砸在所有人的心湖里。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他……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张团长赶紧回头,用胳膊肘捅了捅我,急得满头是汗:“老王!首长问你话呢!”
我这才如梦初醒,下意识地向前一步,立正站好,挺起胸膛,大声回答:“报告首长!机务大队一级军士长,王建国,到!”
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以军人的身份,向上级报告了。
那位将军,缓步走到我的面前。
离得近了,我才看清他的脸。大概五十多岁的年纪,面容清癯,眼神深邃得像一片星空,仿佛能洞穿人心。他的肩章,是一颗闪亮的金星。
中将!
我的呼吸都停滞了。一个中将,空军总部的首长,竟然……竟然认识我?
周围的领导们,更是连呼吸都快忘了。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总部的大首长,会连夜坐专机来到这个偏远的戈壁机场,就为了见一个即将退伍的老兵。
张团长站在一旁,手心里的汗,已经把白手套都浸湿了。
那位将军没有说话,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
他的目光,先是落在我满是皱纹的脸上,然后是我洗得发白的军装,最后,停在了我那双布满老茧和油污,甚至有几根指甲因为常年接触化学试剂而微微变形的手上。
他盯着我的手,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整个停机坪,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运输机引擎冷却时发出的轻微“咔哒”声。
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心里更是翻江倒海。他到底是谁?他来找我做什么?
就在我快要绷不住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
“我是空军装备部,陈振邦。”
空军装备部部长!
这七个字,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炸开。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可是真正的大人物!主管全空军所有飞机的研发、采购、维护和保障!跺一跺脚,整个空军都要抖三抖的顶尖大佬!
张团长更是吓得脸都白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递上去的那份看似普通的退伍申请,竟然会惊动这样一尊大神。
我更是如遭雷击,呆立当场。
我王建国,一个大头兵,怎么可能和这种级别的人物扯上关系?
陈振邦部长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他的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我。
他突然伸出手,不是跟我握手,而是轻轻地托起了我的右手。
他用他那干净、温暖的手掌,包裹住我这双粗糙、冰冷、沾满了二十八年风霜油污的手,用指腹轻轻摩挲着我手背上的伤疤和老茧。
那动作,不像是一个将军在对待下属,更像是一个顶级的工匠,在欣赏一件举世无双的珍宝。
所有人都看呆了。
“好一双手啊……”陈部长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和……愤怒。
他抬起头,目光重新变得锐利如刀,扫过我,又扫过我身后的张团长和一众军官。
“王建国同志,”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二十八年,为国修机,劳苦功高。现在,你想就这么一走了之?”
他顿了顿,另一只手缓缓伸向身后秘书递过来的一个红色封皮的文件夹。
他将文件夹拿到我面前,用手指重重地敲了敲封面。
“你想走,问过我手里这个东西,同意没有?!”
第六章:一张特殊的“考卷”

那一声质问,如同平地惊雷,在寂静的停机坪上空回荡。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陈振邦部长手中那个红色封皮的文件夹上。
那是什么?
处分决定?还是……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文件夹,心脏狂跳,大脑一片混乱。我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陈部长看着我惊疑不定的眼神,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意。他没有立刻打开文件夹,而是转头看向那架刚刚完成大修,静静停在不远处的“飞豹”战机。
“张团长。”
“到!”张团长一个激灵,赶紧应道。
“那架‘飞豹’,就是王建国同志负责维修的?”
“报告首长,是的!那是我团故障率最高,也是维修难度最大的一架飞机,之前一直小毛病不断。这次经过王建国同志亲手大修,所有数据都恢复到了出厂峰值!”张团长赶紧抓住机会,为我表功。
陈部长点点头,又转回头看着我,眼神变得意味深长。
“王建国同志,听说,你是我们空军最顶尖的‘飞机医生’,任何疑难杂症,到你手里都能手到病除?”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硬着头皮回答:“报告首长,不敢当。我只是……尽一个机务兵的本分。”
“好一个本分。”陈部长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然后突然话锋一转,“既然如此,我这里,也有一道‘题’,想请你这位‘神医’,给看一看。”
说着,他朝身后的秘书使了个眼色。
那名秘书立刻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了一台军用笔记本电脑,迅速开机,然后将屏幕转向我。
屏幕上,是一段视频。
视频的画面在剧烈地抖动,背景是高空中的云层,还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和飞行员急促的喘息声。这……这是战机驾驶舱的飞行记录仪画面!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视频里,一架外形极其科幻,我从未见过的新型战机,正在空中做着剧烈的机动。但它的动作,明显不正常,带着一种濒临失控的僵硬。
“……左侧副翼响应延迟0.5秒!液压系统压力不稳,在临界值波动!请求返航!请求返航!”飞行员的声音充满了焦急。
“稳住!稳住!尝试手动配平!”地面指挥塔的声音传来。
画面中,飞行员艰难地操控着驾驶杆,但飞机依旧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难以驯服。
视频很短,只有不到一分钟,最后以飞机艰难地拉平姿态,画面中断而结束。
看完视频,我的后背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
作为一名顶级的机务,我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机械故障,而是一种极其罕见,也极其致命的“复合型耦合故障”。也就是说,至少有两个以上看似毫不相关的系统,在特定的飞行姿态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联动,互相干扰,导致飞控系统出现紊乱。
这种故障,是所有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的噩梦。因为它毫无规律可言,检测难度极大,就像一个潜伏在飞机体内的幽灵,随时可能出来索命。
“怎么样?”陈部长关掉视频,看着我,“看明白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报告首长,初步判断,是飞控系统的舵机响应,与液压系统发生了异常耦合。但具体的原因……需要看到详细的飞行数据和地面检测报告。”
我说得很保守,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这明显是一架还在试飞阶段的,最新式的五代机。它的技术,比我们基地现役的飞机,至少领先一代。
听完我的话,陈部长身边的一位看起来像是总工程师的技术干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显然没想到,一个基层的士官,只看了一段视频,就能如此精准地判断出故障的核心。
陈部长脸上却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数据和报告,我们有。国内最顶尖的专家团队,对着那些数据,研究了半个月,提出了十七种可能性,进行了上百次模拟,但没有一次,能完全复现视频中的故障。”
陈部长的声音,透着一股沉重的压力。
“这架飞机,是我们国家倾注了无数心血,研制出的最新一代‘争气机’。它的性能,全面超越了我们所有的对手。但是,这个‘幽灵’一样的故障,不解决,它就永远无法定型列装。我们……拖不起了。”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恳求。
我明白了。
我彻底明白了。
这不是什么“考题”。
这是一份来自共和国空军装备部部长的……求助!
他连夜赶来,不是为了兴师问罪,也不是为了挽留我这个老兵。
他是来……请我出山的。
他把解决国之重器技术难题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这个只有高中学历,即将被体制淘汰的老兵身上。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看着陈部长那双充满期盼和信任的眼睛,又看了看他手中那个红色的文件夹,一时间,百感交集,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围的领导们,也都听明白了。他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脸上的表情,比见了鬼还要精彩。他们看向我的眼神,从震惊,变成了骇然,最后,化为了深深的敬畏和……羞愧。
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差点让一个怎样的人物,从指缝间溜走。
张团长更是激动得浑身发抖,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眼里已经泛起了泪光。
陈部长没有催促我,只是静静地等着我的回答。
整个停机坪,落针可闻。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二十八年的委屈、不甘、心灰意冷,在这一刻,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责任感和使命感,冲击得七零八落。
我是一个兵。
一个为国修了二十八年战机的兵。
我的天职,就是为战鹰排除一切故障,让它们能够安心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现在,一架最重要,也最需要我的战鹰,“生病”了。
我,能走吗?
我,有资格走吗?

我缓缓地抬起头,迎着陈部长灼灼的目光,那颗早已冰冷死寂的心,在这一刻,重新燃起了火焰。
我没有回答他那个问题,而是反问道:“首长,我能……看看那架飞机吗?”
此话一出,全场皆惊。
陈部长身后的那位总工程师,忍不住上前一步,皱眉道:“王建国同志,这不合规定。这架飞机目前是最高密级,你……”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陈部长挥手打断了。
陈振邦的脸上,绽放出如释重负的笑容。他就知道,他没有看错人。真正的“兵王”,骨子里流淌的,永远是忠诚和担当。
“规定?”陈部长朗声笑道,“今天,我陈振邦,就为王建国同志,破一次例!”
他猛地拉开手中那个红色文件夹的封条,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高高举起,面向所有人。
那是一份烫着金边的命令,抬头是鲜红的“中央军委”字样,下面盖着鲜红的国徽大印。
“中央军委特别命令!”陈部长用洪亮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念道,“兹任命,空军xx基地机务大队一级军士长王建国同志,为‘新型战机攻关项目’特聘技术总顾问,授空军技术大校军衔,即刻生效!”
“轰!”
我的大脑,像是被一颗核弹击中,瞬间一片空白。
特聘……技术总顾问?
空军……技术大校?
我……我提干了?而且是连升N级,直接从一个士官,变成了一个大校?
这……这不是梦吧?
我用力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剧烈的疼痛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
“老王!”张团长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冲上来,一把抱住我,这个铁打的汉子,此刻哭得像个孩子,“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行!”
李浩和那些年轻的机务兵们,也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师傅威武!”
“王师傅牛逼!”
而那些之前对我爱答不理,甚至有些轻视的机关领导们,此刻一个个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任由他们欢呼,任由张团长抱着我哭。我的目光,却始终落在那份特招令上。
二十八年。
我等了二十八年的认可,终于在这一刻,以一种我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方式,从天而降。
陈部长走到我的面前,亲手将那份沉甸甸的任命书,交到了我的手里。
“王建国同志,”他拍着我的肩膀,眼神无比郑重,“欢迎归队。现在,可以带我,去看看你的‘新战友’了吗?”
我看着他,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
我猛地擦干眼泪,双脚用力一并,挺起胸膛,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用尽我此生最大的力气,吼出了那句我以为再也无缘说出的话: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尾声:新的起飞
三个月后,北京西郊,空军某绝密研究所。
在一间巨大的无尘恒温机库里,那架曾经让无数专家束手无策的新型战机,静静地停在中央。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工作服,外面套着白大褂,戴着一副高精度电子放大镜,正趴在打开的机腹下,手里拿着一把特制的探针,小心翼翼地探查着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飞控总线。
我的身边,围着一群平均学历博士以上的飞机设计师和工程师,他们屏息凝神,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打扰到我的工作。
李浩也作为我的助手,被特招进了项目组。他此刻正举着战术手电,为我提供照明,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排查和上千次的数据比对,我终于将故障范围,锁定在了这根隐藏在数百条线路中,极其不起眼的信号线上。
我的理论,依旧大胆得近乎疯狂。
我认为,故障的根源,并非来自机械或电子系统本身,而是来自一种极其罕见的“材料应力疲劳”。这根信号线,在特定的高G机动下,其内部的晶格结构会产生一种人眼和普通仪器都无法察觉的瞬时形变,导致信号出现零点几秒的延迟。而这个延迟,又恰好与液压泵的脉冲频率产生了共振,最终引发了连锁反应。
这个理论,在场的专家们闻所未闻。
“找到了。”我直起身子,摘下放大镜,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机库。
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我指着那根信号线上的一个微不可查的点,对身边的总工程师说:“用高倍电子显微镜扫描这里,放大两万倍。你们会看到,晶格结构上,有一条比纳米还细的疲劳裂纹。”
半小时后,检验报告出来了。
结果,与我的判断,分毫不差。
整个研究所,瞬间沸腾了!
那个困扰了中国最顶尖大脑们近半年的“幽灵”,终于被我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老兵,用最“原始”的办法,给揪了出来。
陈振邦部长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走过来,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
“建国同志,你为国家,立了大功!”
那天晚上,庆功宴上,我破例喝了很多酒。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戈壁滩上的小机场,看到了那些和我朝夕相伴的“铁鸟”,看到了张团长,看到了那些可爱的战士们。
半个月后,那架新型战机,换上了全新的材料总线,再次飞上了蓝天。
这一次,它如臂使指,完美地完成了所有高难度试飞科目。
我站在指挥塔的落地窗前,看着那道优美的银色弧线,在天空中划出一道胜利的轨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的身边,站着同样身穿大校军服的张团长,他也被调到了北京,成了我的副手。
“老王,真有你的。”他感慨万千。
我笑了笑,目光望向更远的天际。
“不,不是我有多厉害。”我轻声说,“我只是,听懂了飞机的话而已。”

天空中,战鹰呼啸。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起飞。而我,王建国,这颗拧了二十八年的老螺丝,终于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恭喜火箭队! 5人训练营正式开启, 3老将带2新人, 饼皇对


《魔兽世界》周年服外域528和328礼包公布,TBC测试已开


香蒲丽防晒霜怎么样适合干皮吗?推荐3款好评如潮的产品!


火箭签下奥科吉,杜兰特加盟,阵容升级冲击总冠军


中耐地基:专业地基加固与沉降修复技术专家


属兔的, 未来十年事业关键期分析